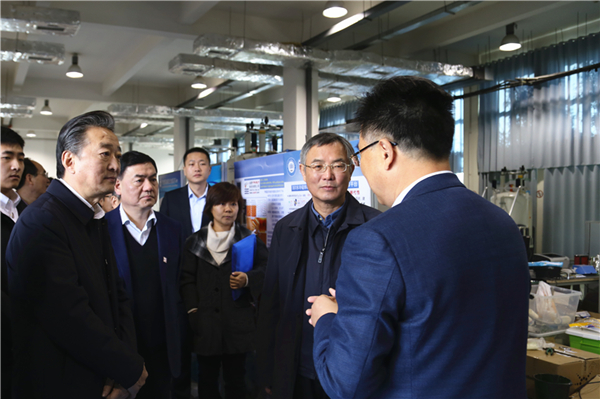冯骥才:画画,是我心灵的方式

《阿尔卑斯山的小屋》
“春天,在我易感的心中呼唤出无穷的画意”。
三年前,冯骥才在他的戊子画展中这样写道。那一次,他展出了六十幅格调清新、笔墨酣畅的国画新作,令人不禁感叹他如何在繁重如山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,还有如此的“闲心”和雅兴。
今年新春,他又将二十余载近百幅绘画作品精选后,出版了一本装帧精美印刷考究的《冯骥才画集》,并在北京举办了隆重的首发式。于是我们终于明白了:画画,不是他的“业余爱好”,而是他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--如果说,写作是他的责任方式的话,那么,绘画更多地是他的心灵方式。所以,只有将他的画和他的小说、他的文化保护联系在一起,才是一个完整的冯骥才。而出版这本大型画册的目的,除了对他的绘画生涯进行一次认真梳理和总结外,也是希望他的画能独立地面对受众,使他们能从纯粹艺术的角度来看待他的作品。
近日,围绕着这一“纯粹艺术”的话题,冯骥才与本报记者进行了一次深入交谈,所阐述的观点不仅独辟蹊径,且新鲜有趣。
一进画室,就进入我的心灵世界
记者:拜读了您最新出版的《冯骥才画集》,我不得不在羡慕之余,再次心生疑问——您目前至少在四个领域里奔波往复,最占时间的恐怕就是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了。例如您花了九年时间,最近刚把二十二卷的《中国民间年画集成》出齐,马上又要开始下一个系列文化工程的运作;您主持着全国非遗专家委员会的工作,日前又连任了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主席的职务。第二,我经常从报纸上看到您发表的文章,虽然小说写得少了,散文、随笔却不少见,而且每年都有新书出版。第三,您在天津大学冯骥才艺术研究院带了五位博士研究生、一位硕士研究生,有文学专业的,也有遗产学专业的。然后呢,您还画了这么多画,出版了这么精美的大画册。所以我首先想问您一个问题:绘画在您的整个生活中占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?
冯骥才:你不是去过我家吗,我楼上有几个书房,都不大,一间是写作的,一间是做民间文化研究的,还有两间是画室。写作的房间堆满书和资料,摆放着许多中外文学家的雕像;研究民间文化的房间到处都是乡土气息浓郁的民间艺术品;画室里自然是充盈着纸香和墨香了。而做什么,有时要听命于心灵的驱动:一上楼,忽然有画画的冲动,就进画室;有写作的灵感,就进书房。有时是写文章和画画交叉进行。
我一旦进入画室,就进入一种心灵生活。当我把画案上的笔洗换了清水,用镇纸将一张像被月光照得皎白的宣纸铺在桌上时,感到宣纸上仿佛布满我的神经,每一笔触到纸上,都如同触到我心灵的深处。这时真的很享受。所以我觉得绘画是我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。哪一部分?是我心灵生活的一部分。我说过一句话:写作更多地是我的责任方式,而绘画更多地是我的心灵方式。当我心中有一种感受,或被什么东西触发了自己的心灵时,才会画画。比如有一年秋天,我看到街道上有一大片落叶,通红的落叶在逆光中连血脉(叶脉)都呈现出来,特别漂亮。这时头脑中忽然忆起一件往事:一次我在加拿大街头散步,一个女孩迎面走来。她走路的姿式很奇怪,像跳舞似的,左跨一步,右跨一步,有时两腿还别一下。走近了才知道,她是不忍踩踏路上的红叶而躲着它走的!我被这种对生命和美的怜爱所打动,于是画了一幅落叶图,画题是《每过此径不忍踩》。这就是我画画产生的一个原点和最初的冲动——触动的不是感官,而是心灵。
记者:记得您说过,绘画是艺术家心灵的闪电,而您的一些画作,就是直接表现心灵、思绪甚至思维的,如《思绪如烟》、《枝乱我不乱,从容看万条》等,将思维变成了可视的形象。你为何喜欢表现这些思维层面的东西?
冯骥才:有一次我画了一片树枝,粗细深浅不一,相互穿插有序有人问我:你这幅画画的是什么?我说:“画的是思维”,他有些迷惑不解,我告诉他:有一次我自己坐在椅子上,喝着茶,半闭眼睛思考一些理性的问题。这些纯理性的东西像哲思一样,沿着一个思维线索和逻辑推理走下去;走到一定时候,又冒出一个新的灵感,仿佛出现了枝杈,新的线索又出现了。想着想着,横向里又切入一条线索,把原来的思维打断了。这时,远远又见另外一个思维渐渐走近……我发现,理性的大脑也会出现如此美丽的形象和状态。我喜欢这样的作画缘起与过程。

《解冻》
我作画时还有一个“毛病”:必须有音乐相伴。比如我忽有激情,想画一深谷疾瀑,把纸按在墙上便开始放音乐。我选择李斯特的狂想曲,惟有他能唤发我此刻的创作激情。如果当时未画完,晚上继续再画时,如何把情绪连贯起来?一放李斯特的音乐,马上找到了当时的感觉。绘画是一种美好的心理享受,所以我认为绘画不是一种职业,甚至不是一种专业。
绘画,就是不断尝试新的可能性
记者:您认为绘画不是一种职业或专业,这个观点我觉得很新鲜。这是否因为您身兼多职,客观上也不可能把绘画当成一种职业?
冯骥才:实际上,我做任何事情都会全身心地投入。绘画不是我写作的“业余”,写作也不是我文化保护的“业余”。不久前我在北京《冯骥才画集》发布会上说过,我对文字有巨大兴趣,没有任何东西比文字更能精准地表达我们的思想和感受。我对文字的要求是苛刻的。所以我的文字稿一般是改七遍,而且最后两遍是修改文字(不是修饰,而是选择文字),以便更准确地表达我的想法。一个作家要不断用文字深化自己的思想和感受,表达得越精准越好。
一个画家作画时,是不断尝试各种新的可能性。因为绘画的必然性已被前人尝试过;凡是被人尝试过的成功的,都是一种必然。如古代画家关左、范宽,都把高山深谷松林大壑表达出来了,变成了一种必然。另外的画家就要有另外的审美角度,如倪云林就表现了一种宋代画家没有表现过的东西,一种苍凉、荒寒却又优美的心境……绘画就是要不断表现这种可能性。这种努力有两个方面,一是横向的可能,大都是视觉上的;二是纵向的深度、心灵的深度。我更喜欢后者,即前人未表现过的东西,如人内心的一些感受。为什么?因为我是一个文人,文人的内心世界要非常丰富,他的人生经历、人生感受,包括那些亦苦亦甜、亦美亦丑的感觉、百感交集的感觉,都能在他笔下栩栩如生地描写出来。特别是小说家,对人的感受一定会更丰富。一个短篇写几个人物,中篇写十几个人物,长篇写几十个人物,每个人物的身分、地位、性格、命运、心境都千差万别,作家都需“钻”到他心里。所以作家对人物内心的体验比一般人要深刻得多、丰富得多、广阔得多。作家内心的丰富性,是我绘画中最重要的原点(资源)。
绘画的文学化才是中国画的本质
记者:在您的《文人画宣言》中,曾以王维的“诗中有画,画中有诗”和郑板桥的“一枝一叶总关情”为例,概括出处画的两个重要属性:文学性和直抒胸臆。几年过去了,您对文人画有哪些新的认识和感悟?
冯骥才:什么是文人画?我觉得文人画首先应是一种张扬个性和直抒胸臆的绘画。我们研究一下中国绘画史,我认为可分三个时期:一是画工时期。敦煌壁画那个时期主要是为宗教作画,一直到唐代的吴道子、王维、周昉,是画工中的大师和高手,有很高的绘画风格和技巧,但他们不是为自己画画。第二个时期是画院时期。从董源、范宽到马远、夏圭,在画院任职,为皇帝和贵族作画。他们把中国画技术推到一个极致,但仍不是为自己作画、画自己的心灵。从宋代开始,出现了一批为自己画画的文人,他们是苏轼、米芾、文仝。他们的画没有多高的技巧,当时称之为“隶家画”,带有贬义。到元代,倪云林提出一个概念:画画是“抒发胸中之逸气耳”,这时才出现了真正的画家,画家一出现就是文人画。文人画出现之后,绘画的一个新概念也应运而生,即“意境”。“意境”是什么?这两字是要拆开来解的,“境”即空间的境像,“意”即画家的主观意念、意味、诗意,“意境”即把绘画文学化。所以,绘画的文学化才是中国画的本质。

《水村》
记者:听您这么一讲,真有一语中的、茅塞顿开的感觉。可是怎样才能使绘画作品有内涵、有意境呢?毕竟,绘画文学化的高度是一般画家难以企及的。
大冯:我认为当代中国画的最大问题是技术主义,即把技术的、视觉的因素放在第一位,忽视了对意境和内涵的追求。所以现在的中国画看起来彼此雷同,许多画家只是技术好,层次和境界却有局限。前些日子,一位美院老师对我讲,他们最爱看视觉性的绘本,我说,你们最大的问题是不能穿越绘本,就是杜牧说的“功夫在诗外”,“开口必言诗,定知非诗人”。搞艺术的人最重要的还是对世界、对人生、对人的看法。你的人生阅历越丰富,人生感悟越深刻,绘画的底蕴自然越深厚。在这一点上,我很欣赏何家英。因为工笔画要求很高的技术性,尤其工笔人物,第一受具像的限制,第二受技术的限制,如能将工笔人物画得有意境、有内心的呈现就太难了。但何家英做到了。这是他对人物画的贡献的根本所在。
一天到晚画画,绝画不出好画
记者:又回到最初的话题:您身兼多种社会角色,工作非常繁忙,您如今挤出时间,让自己的心灵在绘画的世界里自由翱翔呢?
冯骥才:画画与我的其他事情,可能在时间上是有冲突的,但在总体上没有影响,甚至还有帮助。我还有一个理解:如果一个画家一天到晚画画的话,他绝对画不出好画来。道理是:如果他只埋头作画,会遇到两个问题:第一,一个画家最难突破的是自己创造的一整套创作习惯和审美形式,你的形式越成功就越难突破,艺术最难的就是突破自己;第二,画来画去就没感觉了,审美疲劳了。就像你用手抚摸一件东西,觉得那东西光滑、细腻,手感很舒服,如果把手一直放在那儿,那种美好的感觉就消失了;只有把手离开,待会儿再摸才有感觉。所以,一个画家不要死盯着自己的画,而应去观察世界,感受生活,学会思考。画家不要总去看画,而要看一些看似无关的非视觉的东西,比如各种书籍。牛之所以长牛肉,不是因为吃牛肉而是吃草。
(责任编辑:夏传磊)